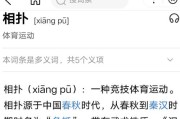人性之光:在"人皆有之"的普遍性中寻找文明的根基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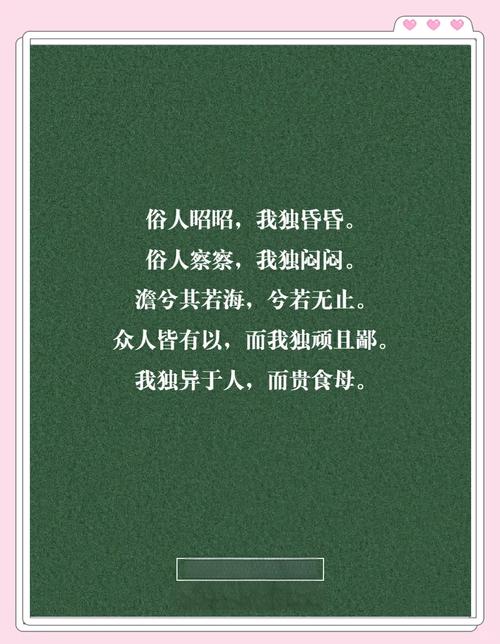
"人皆有之"——这简单的四个字蕴含着人类文明最深刻的智慧。从孔子的"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"到康德的普遍道德律令,从世界各大宗教的黄金法则到现代人权宣言的基本精神,人类历史上那些最璀璨的思想结晶无不指向一个共同点:那些真正有价值的事物,应当是所有人都能拥有、都应拥有的。这种普遍性的理念,构成了人类文明的道德基石,也是我们对抗偏见、歧视与不平等的精神武器。在这个日益分裂的世界里,重新思考"人皆有之"的哲学意义,或许能为人类共同的未来指明方向。
人类思想史上对普遍人性的探索从未停歇。孟子言"人皆有不忍人之心",认为恻隐、羞恶、辞让、是非这"四端"人人生而具备;古希腊斯多葛学派主张世界公民理念,认为理性为所有人共有;18世纪启蒙思想家高举"人生而平等"的旗帜,将普遍人权理念播种于现代政治土壤。这些思想虽然诞生于不同时空,却惊人地指向同一个真理:在本质层面上,人类共享着某些基本特质与权利。法国大革命时期《人权宣言》之一条规定:"人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的,在权利上一律平等。"这种宣言不是对现实的描述,而是对理想的宣誓,它基于的正是"人皆有之"的信念——某些权利不应是某些人的特权,而应是所有人的标配。
"人皆有之"的理念在当代社会面临着严峻挑战。物质层面上,我们生活在一个资源分配极度不均的世界——据乐施会报告,全球最富有的1%人口拥有近一半的全球财富,而最贫困的50%人口几乎一无所有。精神层面上,种族主义、性别歧视、地域偏见等思想仍在制造人为的区隔与不平等。更值得警惕的是,这种不平等往往被合理化、常态化,甚至内化为社会共识。当某些人认为优质教育、体面医疗、有尊严的生活只是"某些人"的专利时,"人皆有之"的理想就被扭曲为"人皆可有之"的现实妥协。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·森曾指出,贫困不仅是收入的剥夺,更是能力的剥夺,是参与社会基本活动的自由被剥夺。这种剥夺正是对"人皆有之"原则的背离。
从哲学层面看,"人皆有之"反映的是一种普遍主义伦理观,与特殊主义、相对主义形成鲜明对比。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提出的"轴心时代"理论指出,公元前800至200年间,中国、印度、波斯、犹太和希腊等文明几乎同时出现了对普遍人性的思考,这是人类精神的之一次大觉醒。这种觉醒的核心,正是认识到在种族、阶级、性别等表面差异之下,存在着某种共同的人性基础。犹太哲学家马丁·布伯的"我-你"关系理论强调,只有当我们把他人视为与自身平等的"你"而非客体化的"它"时,真正的人际关系才成为可能。这种认识要求我们超越狭隘的自我视角,看到他人身上与自己相同的本质——这正是"人皆有之"理念的精髓。
在实践层面,"人皆有之"应当成为社会制度设计的指导原则。北欧国家的社会福利模式之所以备受推崇,正是因为它试图确保教育、医疗、养老等基本需求真正成为人人可享的权利而非待价而沽的商品。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(SDGs)的核心精神也是"不落下任何一个人",这体现了全球层面对"人皆有之"理念的认同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"大同"理想,《礼记》描述的"老有所终,壮有所用,幼有所长,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"的社会图景,与这一理念高度契合。构建这样的社会,需要的不仅是资源再分配,更是观念上的革命——从"某些人有之"到"人皆有之"的认知转变。
"人皆有之"的理念在今天具有特殊的时代意义。面对气候变化、疫情流行等全球性挑战,人类命运从未如此紧密相连。病毒不分国界,温室效应不认种族,这些危机以其残酷的方式提醒我们:在生存面前,人类是一个整体。法国作家加缪在《鼠疫》中写道:"在灾难中,人们认识到存在某种他们共同拥有的东西。"这种共同拥有的东西,正是我们的人性本身。全球问题的解决需要全球合作,而合作的基础是承认我们共享某些基本关切、权利与责任——这正是"人皆有之"理念在当代的延伸。
回望历史长河,人类文明的进步往往以"人皆有之"范围的扩大为标志——从贵族到平民,从男性到女性,从主流群体到边缘群体,权利的阳光逐渐普照更广阔的人群。这一进程远未完成,但方向已经指明。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《卡拉马佐夫兄弟》中写道:"每个人都对一切人和一切事负有责任。"这种看似夸张的表述背后,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刻直觉。当我们真正理解"人皆有之"的深意,我们就能超越狭隘的利己主义,看到自己与他人之间那看不见却真实存在的纽带。
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,让我们回归"人皆有之"这一简单而深邃的智慧。它提醒我们,无论肤色、信仰、国籍如何不同,在欢笑与泪水、希望与恐惧、对尊严的渴望与对压迫的抗拒上,人类共享着相同的情感与诉求。承认这一点,不是否认多样性,而是在差异之下发现更深刻的统一。唯有建立在这种认知基础上的文明,才能真正实现"各美其美,美人之美,美美与共,天下大同"的理想境界。人性之光,普照众生——这或许就是"人皆有之"给予我们的最珍贵启示。
 富贵体育网
富贵体育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