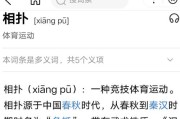谤讥于市朝:当语言成为权力的暴力工具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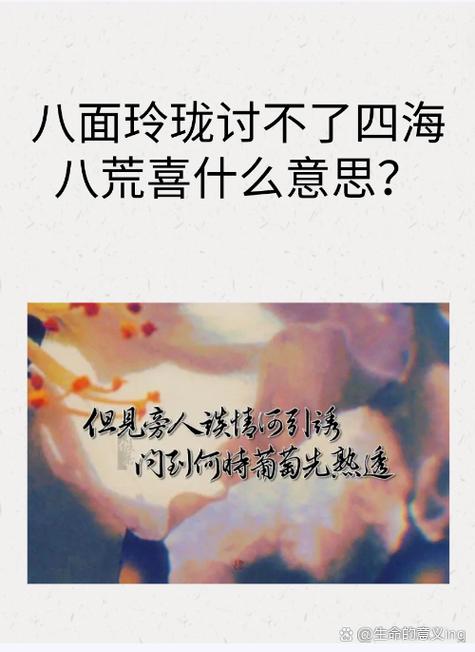
"谤讥于市朝"出自《左传·襄公二十七年》,原文为"谤讥于市朝,闻于诸侯"。短短八字,却勾勒出一幅古代社会舆论暴力的生动图景。表面看来,谤讥不过是市井间的闲言碎语、朝堂上的讥讽批评,实则暗藏着一套精密的权力运作机制。当我们穿越时空的迷雾,重新审视这一古老词汇,会发现它揭示了一个永恒的命题:语言如何成为权力的暴力工具,而作为现代人的我们,又如何在这片语言的荆棘丛中寻找文明的出路。
谤讥二字,拆解开来各有深意。"谤",《说文解字》释为"毁也",指无中生有的诋毁;"讥",《说文》释为"诽也",意为含沙射影的讽刺。二者结合,构成了一种特殊的语言暴力——它不同于直接的武力压制,而是通过扭曲事实、制造舆论、操控人心来实现社会控制。在古代中国,市朝是信息传播的核心场域,市井街巷与朝廷议政之地共同构成了舆论发酵的温床。谤讥之所以能"闻于诸侯",正是因为这种语言暴力具有极强的传染性和破坏力,能够在社会 *** 中迅速扩散,最终影响权力格局。
历史长河中,谤讥作为权力工具的使用案例俯拾皆是。战国时期,张仪游说各国,常以谤讥之术离间敌国关系;三国时代,曹操"挟天子以令诸侯"的同时,也深谙谤讥之道,通过舆论塑造自身正统形象而贬低对手。这些案例揭示了一个残酷真相:谤讥从来不是单纯的言语表达,而是裹挟着明确政治目的的符号暴力。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曾指出,语言不仅是沟通工具,更是权力斗争的场域。在中国古代,谤讥正是这样一种被权力浸染的语言,它通过扭曲的叙事建构现实,使无辜者蒙冤,使真相被遮蔽。
谤讥之所以能成为有效的社会控制手段,源于其独特的作用机制。首先,它利用了人性的认知弱点——人们往往更容易相信*,心理学称之为"负面偏好"。谤讥通过夸大或虚构目标的缺陷,迅速占领公众心智。其次,谤讥常常借助权威渠道传播,如古代通过官吏、士大夫之口,现代则可能通过媒体、 *** 大V等,赋予谣言以表面可信度。最重要的是,谤讥制造了一种群体压力,使个体出于从众心理或恐惧而不敢为被谤讥者辩护,形成沉默的螺旋效应。明代海瑞曾上书直言:"近来士风日下,谤讪成习",正是对这种群体性语言暴力的深刻洞察。
从文化心理角度审视,谤讥现象与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密不可分。费孝通先生在《乡土中国》中提出的"差序格局"理论,为我们理解谤讥提供了钥匙。在一个人际关系紧密、重视面子的社会里,声誉就是社会资本,而谤讥正是对这种资本的蓄意破坏。同时,儒家文化中"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"的道德要求,反而为谤讥者提供了武器——他们可以高举道德大旗,以"批评"之名行"诽谤"之实。这种语言暴力往往披着正义外衣,使受害者陷入"越辩解越可疑"的困境,如宋代苏轼遭遇"乌台诗案"时,政敌通过曲解其诗句罗织罪名,正是谤讥的典型运用。
当代社会,谤讥并未随着文明进步而消失,反而因技术发展获得了新形态。 *** 时代的"键盘侠"、热搜上的"舆论审判"、朋友圈里的"道德绑架",无不是古代谤讥的数字化变种。不同的是,信息传播的速度和广度呈几何级数增长,使得语言暴力的破坏力空前增强。从某明星因 *** 谣言抑郁而终,到普通教师因断章取义的视频遭遇网暴,现代版"谤讥于市朝"每天都在上演。更可怕的是,算法推荐形成的"信息茧房"让谤讥更容易在同质化群体中形成回声室效应,不断自我强化。
面对这一绵延千年的语言暴力传统,我们该如何构建防护机制?法律层面的*立法固然重要,但更深层的解决之道在于文化心理的重塑。首先需要培养公众的媒介素养,使人们具备识别谤讥的信息鉴别能力。其次,建立健康的舆论生态,鼓励就事论事的理性批评, *** 人身攻击的恶意诽谤。最重要的是,每个个体都应保持苏格拉底式的反省精神,在参与舆论前先问自己:我传播的信息是否经过核实?我的言论是否可能伤害无辜?我的批评是出于公义还是私愤?
语言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,也是最危险的武器。"谤讥于市朝"现象提醒我们,文明的真谛不在于消灭分歧,而在于学会如何文明地表达分歧。从春秋时期的市井流言到今天的 *** 暴力,人类在语言暴力的泥沼中挣扎了太久。当我们重新审视"谤讥"这一古老词汇时,实际上是在审视我们自己——是否仍在使用语言作为伤害他人的工具?是否仍在不自觉中成为语言暴力的帮凶?
在这个意义上,破解"谤讥"之谜,不仅是对一个文言词汇的解读,更是对一种文明困境的突围。只有当语言回归沟通本质,当批评保持理性边界,当舆论场域建立起有效的自净机制,"谤讥于市朝"这一绵延千年的社会病态才可能真正走向终结。而这,需要每一个使用语言的人的自觉与努力。
 富贵体育网
富贵体育网